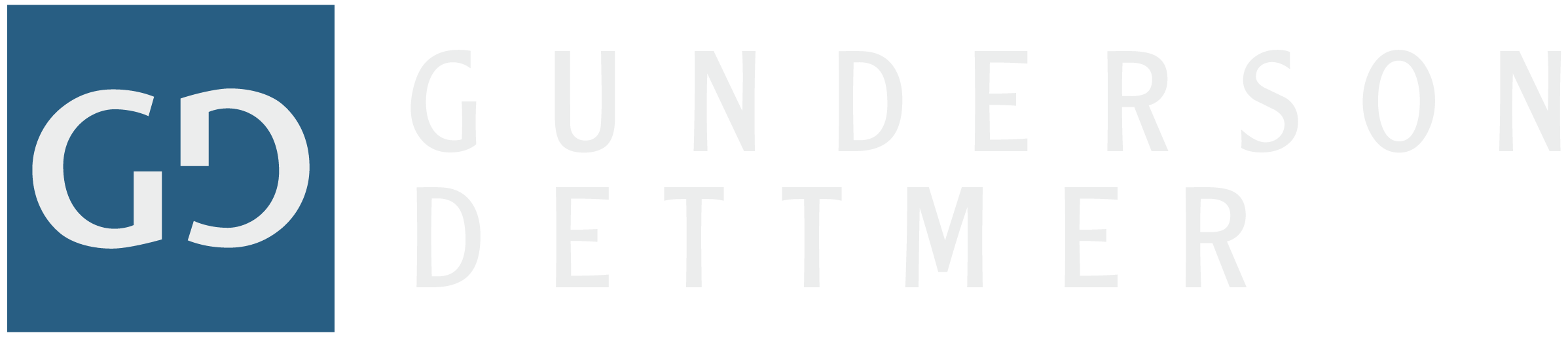美国对华投资限制渐明朗:中国高算力大模型公司或被禁止投资
概述
近日,此前备受关注的反向CFIUS制度有了重要立法进展。2024年6月21日,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发布了《拟议规则制定通知》(“通知”),提出了拟议规则(“拟议规则”,或“规则”)以实施2023年8月9日拜登总统发布的第14105号行政令《关于处理美国在受关注国家的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投资》( “行政令”)。拟议规则进一步细化了2023年8月9日财政部发布的《拟议规则预先通知》(“预通知”),旨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或禁止美国对“受关注国家” (目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及澳门)关键科技领域内的投资。通知发布后,公众有45天的意见反馈时间,提交反馈的截止日期为2024年8月4日。在征求公众意见后,财政部将根据反馈的情况,进一步修改拟议规则,或者发布“暂行最终规则”(interim final rules)或“最终规则”(final rules)。最终规则预计将在2024年年底落地,但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与行政令和预通知一致,拟议规则中规定的投资限制适用于美国人在三个关键领域的对华投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根据被投资对象的业务领域,美国人的投资可能会被视为“需申报的交易”或“禁止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
(1)拟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涵盖的交易”的范围,首次将可转债和或有股权的转股定义为一项单独的交易(区别于可转债和或有股权的获取)。因此,在拟议规则的语境下,最终规则生效前存在的可转债和或有股权在最终规则生效之后发生的转股,也将被视为一项“涵盖的交易”。
(2)针对在何种情况下美国有限合伙人在投资基金中的投资可以被视为“例外交易”,财政部在拟议规则中提出了两种备选方案——方案一规定,美国有限合伙人作为被动投资人的投资构成“例外交易”,前提是其投资额不超过基金管理总资产的50%,或其获得了不参与禁止类投资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方案二规定,美国有限合伙人进行的投资额不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构成“例外交易”。
(3)预通知阶段,财政部仅考虑禁止美国人在一种类型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即开发“专门/主要用于军事、政府情报或大规模监控的最终用途”的AI系统。但此次拟议规则将禁令范围扩展到了对开发前沿AI大模型领域的投资。如果最后生效的正式规则沿用这一禁止类别,那么美国投资人或将无法参与绝大多数从事先进大模型开发的中国公司的未来融资。
为了方便您参照,我们在附录1中列出了拟议规则的核心内容。
自通知出台以来,我们收到了许多来自投资机构和创业公司的问询。本文总结和回应了一些投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与投资实践切实相关的问题。我们理解,财政部会对此次收集到的公众反馈意见做出回应,并有可能对拟议规则中的规定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因此,随着后续规则的修订和出台,我们可能会对本文中的分析做出更新或补充。
重点问题与解答
问题1:与预通知相比,此次拟议规则体现了哪些关键的修改和新增内容?
高锐:此次通知大致延续了行政令和预通知的总体框架。拟议规则针对预通知阶段收到的公众反馈进行了更明确的规定,并且在某些方面对投资限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充。具体而言,此次拟议规则做了以下调整:
- 增加了需申报和禁止交易的类别。比较显著的调整是将对满足不同算力门槛的AI系统的投资纳入了需申报和禁止的范畴。此外,拟议规则在其他两个领域也增设了禁止类别,主要涉及先进封装设备、极紫外光刻制造设备的商品、材料、软件或技术,以及用于军事、政府或监视用途的量子网络或通信系统。
- 强调了美国人对其“受控外国实体”的合规义务。一方面,拟议规则细化了美国人对其“受控外国实体”负有的合规义务,要求美国人采取“合理步骤”来阻止这些“受控外国实体”从事被禁止的交易,包括行使股东权利、开展定期培训和强化内控措施等。另一方面,拟议规则对“受控外国实体”的定义进行了细化。具体而言,“受控外国实体”是指符合以下条件,在美国境外成立的实体:(1)美国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超过50%表决权或董事会投票权,(2)美国人担任普通合伙人、管理成员,或(3)(对于任何集合投资基金实体来说)美国人担任投资顾问。
- 细化了作为美国人承担义务前提的“知悉”标准。拟议规则细化了美国人的“知悉”标准,对知道、有理由知道等情形进行了列举,尤其强调了美国人须对交易进行“合理且勤勉的尽职调查”(见附录1中“知悉”的定义)。如果美国人未在交易时做“合理和勤勉的尽职调查”,而相关交易恰好属于被禁止的交易,那么美国人会被财政部视为“知悉”,而该交易可能会构成对投资禁令的违反。
- 规定了美国有限合伙人在投资基金时的两种“例外”方案。拟议规则明确提出了属于“涵盖的交易”的美国有限合伙人在基金中的投资场景,并且规定了两种“例外”方案:(1)方案一规定的“例外”情形为,美国有限合伙人的投资属于被动投资,且该投资的投资额低于基金募资总额50%的比例门槛,或其在投资基金时获得了普通合伙人不从事禁止类交易的承诺;(2)方案二规定的“例外”情形为,美国有限合伙人对基金的投资金额低于100万美元。 方案一较为宽松,而方案二或将涵盖大多数美国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见下文中关于“问题8”的解答)。
问题2:根据已出台的行政令、预通知和通知,潜在受影响的主体主要包括哪些?
高锐:投资限制适用于“美国人”。需要注意的是,规则对“美国人”的定义比通俗意义中的美国人或美国主体的范围更宽泛。
具体而言,“美国人”包括以下主体:
- 美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无论身处何地):这意味着,如果一家中国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拥有美国国籍或者是绿卡持有者,那么这位创始人将构成“美国人”,因而需要遵守规则下的投资限制。
- 在美国设立的实体及其外国分支机构:中国公民在美国设立的公司及其海外分支机构都构成“美国人”,因而需要遵守规则下的投资限制。
- 在美国境内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无论国籍):该定义在行政令和预通知阶段就存在较大争议。许多中国投资机构尤其担心这种规定会限制投资人员的相关活动,比如出差至美国、在当地了解美国创业项目和做出相关决策等。通知未对这种情况做出排除。
如上所述,被认定为美国人“控制”的外国实体(主要指美国人的海外子公司或其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外国基金)也会受到投资限制的约束。 具体而言,“受控外国实体”是指美国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超过50%表决权或董事会投票权、担任普通合伙人或管理成员、或(对于任何集合投资基金实体来说)担任投资顾问的海外实体。“美国人”应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禁止并防止其海外子公司或其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基金从事任何被禁止的交易,并且必须报告这些海外实体进行的任何需申报的交易。
在特定情况下,投资禁令也会影响有“美国人”担任高管董事或高管、且参与投资决策的非美国实体。通知规定,“美国人”不能“在知情情况下指示”(knowingly direct)(指有权代表非美国人做出或实质性参与决策,并行使该权力指导、命令、决定或批准交易)非美国人进行任何被禁止的交易。
问题3:高锐之前的分析文章提到,行政令明确提到不溯及既往。根据此次通知,在最终规则生效之前发生的交易仍然不受相关规定的影响吗?
高锐:是的。与行政令和预通知的口径一致,财政部在通知中重申,投资限制的规定不会回溯性地适用于在最终规则正式出台之前已经完成的投资交易。但是,最终规则出台之前,在不同时间段内做出的资本承诺(capital commitments)会受到不同的程度的影响:
- 在2023年8月9日行政令发布日期之前确认的资本承诺原则上不受任何影响。目前的规定既不要求投资人撤回现有投资,也不禁止其继续根据之前的承诺为现有公司或投资组合公司提供资金。但需注意之前的资本承诺若采用了可转债或或有股权的形式,则须考虑规则生效后转股的潜在限制(见下文分析);
- 对于在2023年8月9日行政令发布之后至最终规则正式出台之前达成的交易,通知提到财政部可能会要求美国投资人提供相关交易信息。但是,通知没有对需向财政部提供的交易信息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美国人需要根据财政部的具体要求提供所有支持文件。
结合本文其他地方对于可转债和或有股权转股的分析,这里指的在行政令发布前已经确认的资本承诺的后续履约,不包括可转换债券或者或有股权(如SAFE)在规则生效后的股权转换。根据拟议规则,可转换债务或或有股权的股权转换将被视为一项单独的交易。因此,如果股权转换发生在规则生效之后,且原先的资本承诺属于需申报或禁止的交易,那么股权转换本身会被视为需申报或禁止的交易,因而受到最终规则的限制或禁止。
另外,如果被财政部要求提供交易信息,那么投资人或申报人及其相关方需要考虑披露任何信息时可能涉及到的中国法下数据出境、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规问题。
问题4:我们是一个美元投资机构,我们的基金有数名普通合伙人(GPs),其中仅有一名普通合伙人是美籍人士,我们的基金受规则下的投资限制约束吗?
高锐:是的。您的基金由于有美籍普通合伙人的缘故,也需要遵守规则下的投资限制的约束。根据通知中的规定,若非美国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中有美国人,那么无论有几个普通合伙人,该基金都构成拟议规则语境下的“受控外国实体”。这意味着,该基金的美国普通合伙人在基金进行对外投资时需要履行相应的申报义务,并且必须阻止基金进行被禁止的交易。
问题5:我们是一家美元投资机构,已成立了多期基金,其中二期和三期基金投资过被视为禁止类别的交易。在我们即将进行的四期基金的募资过程中,美国有限合伙人(LPs)会被禁止参与投资我们的四期基金吗?
高锐:美国有限合伙人不会被直接禁止投资您的四期基金,但是他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在投资您的四期基金时,并不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它将会开展被禁止的投资项目。换言之,虽然由同一个普通合伙人设立,二期、三期基金在最终规则出台之前开展过的投资项目不会直接影响新设立的基金的新的有限合伙人。但是,新的美国有限合伙人必须对普通合伙人和基金做足够的尽调以了解其投资习惯、常规投资方向、新基金拟投资方向等。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在禁止类领域的投资历史,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是,如果有限合伙人在尽调中获得了可依赖的承诺(比如普通合伙人承诺四期基金不会开展禁止类投资或有限合伙人有权选择不参与此类投资),那么美国有限合伙人也许可以向四期基金进行注资。相反,如果普通合伙人没有做出类似承诺,且其过往基金的投资明显侧重于敏感行业,美国有限合伙人可能会被视为达到了“知悉”标准,且其对基金的投资可能会构成对投资禁令的违反。
问题6:我们是一家美元投资机构。我们目前有一期基金投资了被禁止的项目。根据通知的口径,在这期基金未来的投资项目中,其美国有限合伙人(LPs)会拒绝回应注资通知(“capital call”)且不再入资吗?
高锐:您目前的这期美元基金对禁止类项目的投资可能会使得美国有限合伙人对基金的后续注资构成“禁止的交易”。但是,为满足日后资金需要,这期基金可以考虑采取变通的解决方案。比如,从现有的基金中分离出一支仅有美国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并行基金来投资禁止类及需申报类项目以外的项目标的;或者,由基金向美国有限合伙人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函,承诺他们的资金将不被用于投资禁止类项目。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存在可以变通的解决方案,但相关安排可能会对基金管理人的有序管理以及基金不同有限合伙人之间在账面处理上的投入划分和项目退出分配带来新的挑战。因此,请务必在专业的基金律师协助下完成相关架构的设计和落地。
此外,我们提醒美元基金普通合伙人高度重视基金进行禁止类投资可能给美国有限合伙人造成的声誉风险。我们预计,即便可以通过架构设计使得美国有限合伙人继续参与对各类基金的投资,但很多美国有限合伙人可能会出于对声誉影响的顾虑要求基金管理人承诺完全不参与任何禁止类项目的投资。
问题7:我们的美元基金之前投资了一些AI项目,接下来还准备继续下注这个赛道。我们理解只有对特定类别的AI项目进行投资才是受限制的,此次拟议规则对此有做任何调整吗?
高锐:此次拟议规则所做的最重要的调整之一,就是扩大了受投资限制的人工智能领域。如您提到的,之前的行政令和预通知所涉范围较小,只禁止美国人投资一种类别的AI业务,即开发“专门/主要用于军事、政府情报或大规模监控的最终用途”的AI系统。但是,在这类AI业务以外,此次拟议规则将开发“训练过程中达到了特定算力门槛的AI系统”也列为了受限制的领域。目前通知对禁止类交易规定了三个不同的训练大模型的算力门槛(分别为10^24, 10^25, 和10^26次计算操作),最终规则将会选择其中一个算力门槛作为标准。根据我们与业内人士和投资人的沟通,10^24属于较低的门槛要求,一些小规模的开源模型已经能够达到这个标准;10^25的门槛要求相对较高,不过目前大部分顶尖模型(如GPT-4和Gemini)已经能够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标准。10^25也是目前《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用来判断大模型是否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标准。而10^26标准较高,目前尚未有足够公开数据来确认是否有模型达到或超越,但有人将其与GPT-5作比较,如果将这一算力定为立法标准,今天能符合门槛的中国公司将凤毛麟角。因此,根据目前的已知信息可以基本推断,最终规则更可能采用10^24或10^25作为算力门槛,而覆盖大多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大模型开发公司。换言之,这个禁止类别可能会将目前创投市场上头部投资机构们关注的大多数人工智能公司都囊括进来。其中,几家热度最高、已经完成数轮融资的头部大模型公司都可能被划入禁止投资的范围。这对目前已经投资或原本计划持续投资这些公司的美元投资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财政部在通知中提到,上述禁止类别主要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而不是为了“广泛覆盖仅用于商业应用或其他民用最终用途的人工智能系统”。但不排除主营业务为商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公司由于涉及到大模型的开发而受到影响。
问题8:我听说美国有限合伙人(LPs)对基金的投资在特定情况下属于“例外交易”。因此,并不是所有美国有限合伙人(LPs)都需要担心受到投资限制的影响。请问构成“例外交易”要满足什么条件?
高锐:此次拟议规则对美国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进行了“例外”的规定。财政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例外”方案,符合条件的美国有限合伙人的投资将不受规则限制。在方案一下,如果美国有限合伙人在基金中的出资少于基金管理总资产的50%,或者拿到了基金普通合伙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承诺不将资金用于参与被禁止的投资,且该美国有限合伙人不拥有非被动权力(参与有限合伙人顾问委员会(LPAC)并不必然构成“非被动权力”),那么该美国有限合伙人对该基金的投资可以被视为“例外交易”。在方案二下,投资额为100万美元或以下的美国有限合伙人的投资可以被视为“例外交易”。从覆盖面看,方案一会使得许多有限合伙人对基金的投资成为例外交易,毕竟它们中绝大多数不会作超过基金管理总资产的50%的投资。相反,方案二设置的投资额门槛却又使得过于少数的美国有限合伙人能依赖这个例外规则而被豁免。
我们认为,方案一被最终规则采纳的概率非常小,因为它使得绝大部分的美国有限合伙人都不会受到投资限制的影响,有悖于美国政府制定本规则的初衷。方案二则会使绝大部分美国有限合伙人都无法满足“例外交易”的条件。因此,我们预计有很多相关机构在本次公众反馈的过程中会向财政部提议适当提高方案二中100万美元的投资额门槛,甚至建议结合方案一中“被动投资人”需要满足的几种条件,以达成执法效果上的平衡。
问题9:我们是一个美元基金,持有一家禁止类公司中尚未转股的可转债(convertible bond)。根据原先的约定,这些可转债会在下轮融资发生时自动转股,而下轮融资很有可能在最终规则生效后发生。根据拟议规则的规定,这种早先投资中已获得的可转债在未来的转股会受到规则出台的影响吗?
高锐:行政令和预通知没有对可转债的后续转股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此次拟议规则明确将“或有股权或等效权益或可转换债务转换为股权”这一环节单独列为一项“涵盖的交易”。根据美国财政部再通知中的规定来判断,他们将可转债的转股这一步骤视为一项独立的新决策。因此,如果转股在规则生效后发生,且被投企业属于禁止类项目,那么转股本身将构成一项禁止的交易。这意味着这类可转债需要在规则生效前转股;否则,可能需要转换成单纯的债,由被投公司以现金返还。
我们理解从实操角度来看,“转股是一项单独的投资决策”这一假设是不合理的 ——既没有考虑到在一定先决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转股会自动发生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拟议规则关于“先前确认的资本承诺”的后续履约属于“例外交易”的规定。我们建议关注这一问题的投资机构和初创公司积极利用目前的公众意见反馈期,通过相关机构将修改意见反馈给美国财政部。
问题10:我们美元基金目前的被投公司里有达到需申报条件的公司,也有达到禁止条件的公司。我们还能继续等比(pro-rata)参与这些公司未来的融资吗?
高锐:这是业内人士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个实际问题。其核心在于美国财政部是否会将投资人行使原交易文件中明确约定的等比例参与被投公司未来融资的权利视为“例外交易”中所规定的“基于2023年8月9日前签订的具有约束力且未调用的资本承诺进行的交易”。根据此次拟议规则对可转债的定性,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财政部会把投资人在未来融资中行使优先认购权视为一项独立的新交易的可能性,尤其考虑到投资人既可以选择行使这项权利、也可以选择不行使。因此,如果贵基金考虑未来对这些敏感企业继续注资,就需要严格遵从新规对需申报和禁止投资类型交易的规定。
问题11:拟议规则下,这三个受限或被禁止投资的领域内的中国公司是否仍然可以赴美国上市?
高锐:拟议规则并不直接禁止敏感行业中国公司赴美上市。规则明确豁免了一些投资类型,包括在公开市场通过交易所或场外交易(OTC)购买上市公司的股份。当然,与公司之间协商交易进行的PIPE(private investment in public equity)仍然受到限制而不被豁免。尽管如此,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限制不代表美国投资人和投资银行会无所顾忌地参与此类投资,甚至不代表此类中国公司在美国申请股票公开发行的过程中不会遭遇政策导向性的监管障碍。
问题12:对于需申报的交易,美国投资者需要向美国财政部提交哪些信息呢?
高锐:根据拟议规则,美国人进行需申报的交易应在交易完成之日起不晚于30个自然日内向财政部提交该交易的通知。美国人在交易完成后才获取交易信息并且发现交易构成“涵盖的交易”的事情或情况,应在获取相关信息后不晚于30个自然日内向财政部提交所需的通知。美国人需要在申报时向财政部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美国人的联系信息、交易完后的组织结构图、关于交易商业合理性的说明、对交易涉及到的“涵盖的交易”的简要描述、交易的预期和实际完成日期、交易总价值(以美元表示)、美国人及其关联方在交易完成后对“涵盖的外国人”(包括合资企业)的持股情况、“涵盖的外国人”及其涉及的“涵盖的活动”相关信息,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向财政部提供上述信息可能会涉及到中国法下数据出境、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合规问题。申报方在提交此类信息之前,需要确保遵守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例如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等。特别是涉及跨境数据传输的情况下,申报方需要结合专业数据律师的建议对申报事项进行合规性评估。
问题13:如果违反规定会有什么后果呢?
高锐:根据拟议规则,违规将面临的民事处罚最高可达约350,000 美元或交易价值的两倍。在故意违规的情况下,刑事处罚可达最高20年监禁和最高100万美元罚款。财政部还有权取消任何被禁止的交易,强制要求撤资。
虽然新规尚未实施,但拟议规则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了投资实践中。自行政令颁布以来,很多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已经开始重新评估投资策略,并且调整涉及中国相关领域的投资决策了。这种寒蝉效应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更为深远。尽管如此,如前文分析所示,新规的各种限制仍然有技术上的合理解决方案,建议您积极咨询高锐律师团队及时应对。
本文作者:Gregory Kinzelman、Zhen Liu、Steven Franklin、Richard Chang、David Wang、Silvia Huang
特别致谢Kai Shenghe律师和Chen Gao律师协助汇编。